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五环外OUTSIDE,作者 | 尾火,编辑 | 车卯卯
世界油画,中国大芬
大芬村坐落在深圳布吉镇,俯瞰下去和深圳遍布的城中村大同小异,但走进这里你一定会琳琅满目的“梵高”和“莫奈”所震惊。狭小的街道挤满了各式各样的画廊,光着膀子的画工们就站在巷子里作画,连空气都浸润着油画染料的气息。
这个只有0.4平方公里的客家小村落,是世界三大油画基地之一。这里每年油画出口总额超过5亿元,有一万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师。巅峰时期,这个城中村出品的油画占据了国际市场70%以上的份额。
大芬村不仅仅有着“中国油画第一村”的称号,甚至还曾经被称作中国文化产业的奇迹。但如今,这个传奇小镇正在不可避免地逐渐走向衰败。
01 中国油画第一村的崛起和困顿
从一个只有300个人居住的小村庄,到聚集了上万名画师的全球最大商品油画聚集地,从“大粪村”到“中国油画第一村”,都源自于1989年香港商人黄江的一次决定。
当时黄江带着60多个画工来到这个小村落,在毗邻的大都市深圳的对比下大芬村的环境显得更加恶劣,60多个画工锐减到20多人。当时的黄江还没有长远的规划,也没想着要在大芬呆多久,只想着画油画,然后卖出去。
慢慢地,黄江的画打出了名声,不再仅仅销往香港,开始做起了外销。1992年,一个法国客户给了他36万张画的订单,规定一个半月完成。
“时间紧量又大,我就采用流水线的方式来处理这批画,将20多位画工分为几个部分,分别负责画天、画山、画水和树,同一个人画相同的东西,各幅画差别很小,质量比较稳定,效率也很高。
后来,老外来验货,看到这些画像是复印出来一样,感到很惊讶,也很满意。这事在行业内被传为佳话,我的名声也被广为传播。”
这就是广为流传的“大芬模式”的雏形。
黄江是一个商人,他最初的想法就是:油画能赚钱!
正因此,他催生出了大芬独有的先预定再制作的运作模式。在大芬村,复制油画形成了一条产、供、销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条,画工、代理商和经纪人在这条产业链上分工明确。
大芬村将“订货”放在了第一环节,“大芬模式”的成功是将“艺术”充分市场化的结果。资本是大芬油画等相关产业运行的“血液系统”;而高素质和价格低廉劳动力以及土地资源则是如虎添翼。
在这里,“艺术”因赚钱生产,无数农民工也嗅着金钱和染料的味道寻来。他们放下锄头,提起画笔谋生,成了一个流水线上的“画工”。
正在作画的大芬村画师们
不需要经过系统的美术训练,大芬村的“画工”们大多只经过一两个月的学艺就可以上阵了,最初学艺时,甚至没有报酬。他们挤在狭小炎热的画室里,没日没夜地临摹着世界名画。
大芬村兴起之前,全球的油画工艺品大多来自韩国,那里画师一个月的月薪是20000元,而同样的价格在大芬村可以支付20名中国画师。
再一次,中国制造靠“物美价廉”而取胜。
不同于普通城中村的大芬村
然后现如今,大芬村却也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毕竟,曾经的大芬村快速崛起依赖的就是低廉的人力和土地。而如今即使只是一个城中村,商铺也寸土寸金,工人们也不再像改革开放之处那时拿着吃饱饭的钱就“拼了命”地去画画,再加上随着技术发展电脑喷绘大行其道,人再快也快不过机器。
强依赖出口的大芬村油画产业曾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大受打击,如今的疫情更是让这个小村落雪上加霜。
B站的一个UP主在去年年底去探访了油画村里的一位画师,他边画画边自嘲着说:“过去我画画,一个月是三万两万以上,随便都有。就是觉得很委屈我老婆,认识的时候一个月两三万块钱,现在一个月狂做,一个月才几千块钱。以前是画画来养家,现在赚不到钱了,还要省钱来养画。”
靠价格低廉的复制油画而崛起的大芬村,虽然是中国文化产业的奇迹,但无疑也处在文化产业链的底端,它的前路并不好走。
02 艰难转型的“中国梵高”
2016年,有一部名为《中国梵高》的纪录片在中国和荷兰上映,讲述了大芬村的一位画师赵小勇的故事。
赵小勇专攻梵高,靠着临摹梵高他开了个家庭作坊式的油画店,收了几个徒弟,娶了老婆。他们白天挤在画室里画向日葵,晚上一起看讲述梵高一生的电影。
“我得了病了,我画了这些画,大家都不认同。”电影里梵高疯狂地割下了自己的耳朵,电影外画工们喃喃地重复着这句台词。
赵小勇说,梵高所有的作品他都画过了。《鸢尾花》、《向日葵》他画了两万多幅,订单最多的时候,他一天差不多可以画10幅梵高的画。
在一直合作的一位荷兰画商的赞助下,赵小勇画了20年梵高之后终于有机会抵达荷兰,亲眼看看自己的画买去了哪里和梵高的真迹。
然而巨大的想象落空,一直交易的荷兰画商开的并非一家高级画廊,而是博物馆旁边的一家纪念品商店。赵小勇的一副最小的《向日葵》只要几十块钱,在荷兰的纪念品商店里卖到30多欧元。
当他终于来到美术馆,看到梵高自画像的真迹时,他喃喃自语:“颜色不一样。”第二天,赵小勇找到了梵高的墓,他给梵高墓前点上了三根烟,是感谢,也是告别。
赵小勇给梵高“上墓”
从荷兰回到大芬村后,赵小勇想要放弃临摹,开始创作自己的油画。他说他不想再当画工,想当画家。
赵小勇参观梵高博物馆后的感慨
和赵小勇一样,想从画工成为画家的,还有大芬村。
这个小村落正在深圳征服的扶持下进行自己的产业升级。疫情前,大芬村已经聚集了300多位原创画家,2010年至2015年期间,大芬有近百幅原创作品入选国家、省级美展。
而为了应对租金的高涨,越来越多的大芬村画商们把门店开到了线上。目前大芬有1700多家淘宝店,400多家天猫店,100多家京东店,而微商则是家家都参与的。
如果你在淘宝搜索“油画”,可以看到大部分商家都来自深圳。
原创转型并不容易,大芬村所营造的是市场环境,而非原创艺术环境,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大芬村的画师们被训练的是油画市场供应,而非原创油画艺术创作。而原创画家们来到大芬村也往往会因为欠缺市场竞争力而逃离。
摆在大芬村面前的转型问题,依旧艰巨。这个村落可能是离艺术最近的地方,但也是离创造最远的地方。
03 脚踏大芬,仰望星空
大芬村的土地上,仍在聚集了8000多位文化产业从业者,他们是深圳时代轨迹中的一份子,艺术之于他们是谋生的工具,也是追求的远方。如果他们和这个城中村一起寻找着新的可能性。
曾经的赵小勇们,为了生活疯狂临摹“大师们”的杰作,一幅接着一幅,混淆了日夜,仿佛一个印刷机器。而如今的他们开始尝试自己作画,走上了从“画工”到“画家”,从复制到原创的转型道路。我们并不知道有多少人这其中有多少人能成功,我们着期待他们成功。
因为,这是赵小勇的故事,是大芬村的故事,也是中国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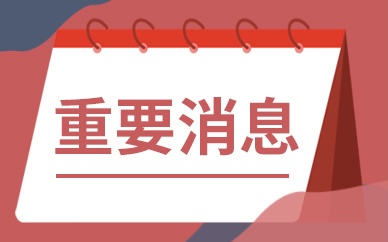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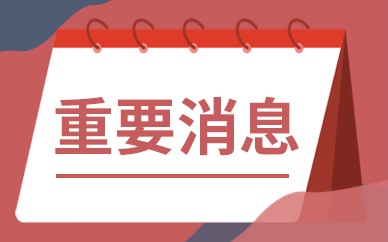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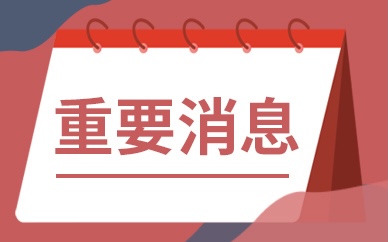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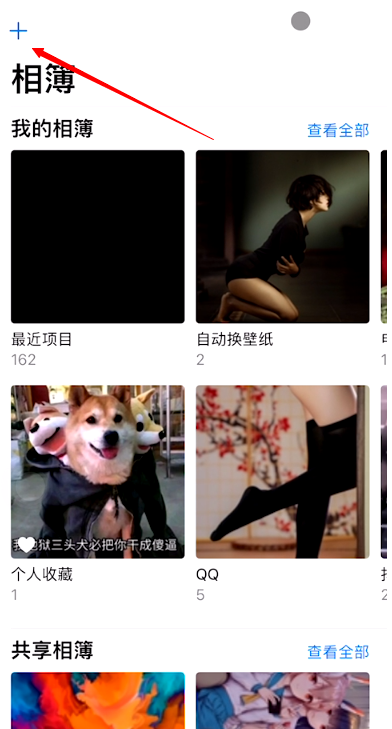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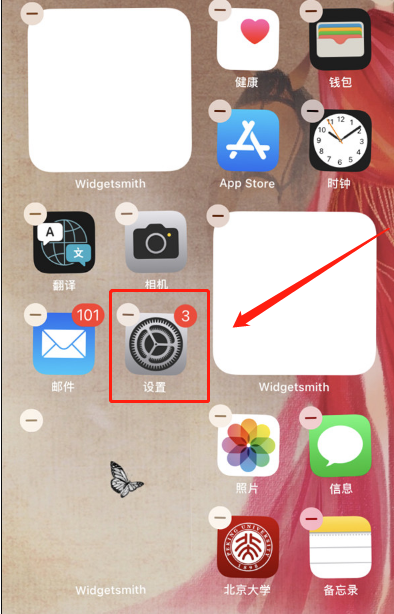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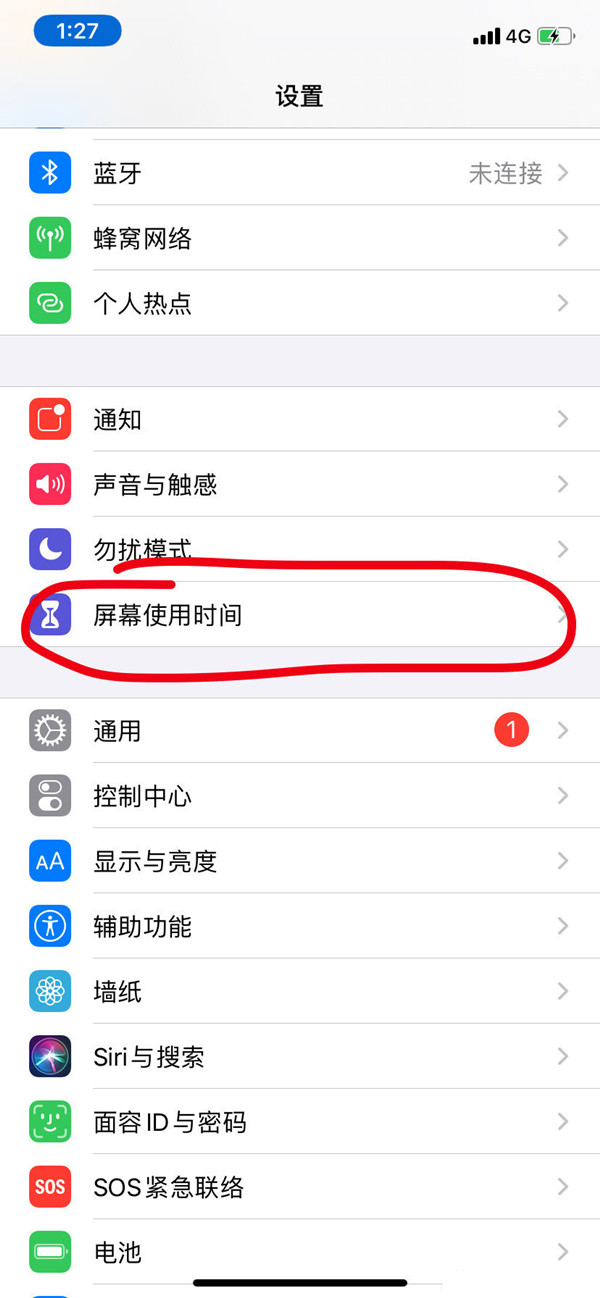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