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巨大的残酷里面,有着巨大的信心。”
《乌海》上映4天,票房不足千万。但对于影片的导演周子陽来说,他还有更在意的事:“我做电影很重要的一点是,能不能过我自己这一关。”
周子陽想做有力量的电影。相比前作《老兽》的苍凉和无奈,《乌海》是更为残酷的,“未必所有人都对残酷的东西有共鸣,我反而是想以这样的方式让人获得更大的警醒和反思。”
他发现很多成功的商业电影都在研究“共情”,以争取更多的观众。在周子陽看来,观众也分好几种,有的人喜欢共情和共鸣,而有的人则需要电影传递出来的思考。前两部长片,他追求的似乎是后者,而之后,他想尝试的是有作者表达的类型电影。
“我以后的电影估计不会比《乌海》更残酷了。”周子陽把他创作的第一个阶段称之为“放黑血”。当人在手腕处有一个内伤、积了一些淤血(黑血),不及时地把这个淤血放出去的话,会造成致死的生命危险。借着《老兽》和《乌海》,周子陽把他身上的“黑血”放了出去。
“我会迈入更客观和成熟的状态再去看待电影。”他说。
在《乌海》上映前,毒眸与导演周子陽聊了聊,以下是他的自述。
“梦境和现实交织在一起”在写《乌海》的故事梗概之前,我大概思考了十几个月,一直琢磨故事方向、人物感觉,就是我称之为冰山之下的部分。所有的剧本都是冰山之下的。这部分是每部电影都会打回原点的。
它会让我思考最本质的东西:电影是什么?我想做的电影是什么?人是什么?人的情感是什么?人的思想是什么?这一点特别有意思。我发现不同的阶段答案会稍微有一些不同,因为你的人生在变化,状态也在变化。
创作《乌海》时,我决定把故事放在三天的时间里讲完,然后开始思考是苗唯(杨子姗饰)多一点还是杨华(黄轩饰)多一点,在启发我创作的那则朋友讲的故事里,男的是行动的那一方,我就对他的心理更感兴趣,他的生活压力更大,我甚至觉得他是弱者,会更想知道他的心理世界,我需要深挖。
思考了十几个月后,我开始写梗概,又花了不到三个月写第一稿,开机前陆陆续续还在改,边筹备边改,改了4、5稿。电影里沙漠月亮那场戏,是我写到那里的时候脑子里蹦出来的,不是构思好的,我也不知道是从哪里生下的印象,很自然地流淌出来了。
在《乌海》中故事发生的三天里,突发事件是杨华面临还账的压力,他要解决这个危机。就像是一个极端事件的倒数24或48小时,我就想展现这个时间段,这几乎都是在极端的状态下的,戏剧性非常强。我需要3-4级台阶,一点一点压到非常合理的方式,然后最后又没有彻底地死掉,我会先这样设计,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创作。
我写(剧本)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醒和睡是交织在一起的,醒的时候写着写着觉得特别累,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好像做梦里面还有一些故事,醒来把梦里的继续写下来,梦境和现实完全交织在一起。
这个过程里,一方面有痛苦在,一方面又有忽然冒出来的一些戏,或者是我更深入的思考。实际上创作的快乐在于有深入的分析和对世界有新的理解,对人有更深的观察。这些是创作之前无法得出的结论。
我在写作的时候有了一个感悟:人不创作就不会产生思想,只有在创作的时候才会真正产生思想。其他时候(的思考)都是过往的习惯或者思维定势在起作用,到不了思想的层面。思想是某种对世界新的认知理性化的一个深度的思考。
整个过程我认为是痛苦居多的,思考本身不是快乐的事情,人都会逃避思考,因为思考很累人,人都是享乐型的动物,所以要逃避思考的煎熬。我写到痛苦的时候觉得生和死都那么回事儿了。
但是当第一稿写出来那天,就只有手指头和脑子在高速地运转,人物,情节,主题,或者突然想到第20场戏、35场戏有一个情节需要改一下,那天就像大爆炸了一样,第一稿就出来了,那一瞬间的愉悦感就超越所有,觉得什么都值了,这是创作带来的巨大的快乐。还挺疯狂的。
《乌海》故事的人物都是复杂的、多面的。就像欠杨华钱的罗宇,他把当地的老人找来演奏音乐,给当地人做了一点事,在他们眼里他是好人;但是作为杨华的哥们,他也伤害了杨华。所以人是丰富的,也有复杂性在里面。
进入每个个体的命运和思想世界时,创作者会面临一些要尝试不同的危险的境地,在创作里边形成巨大的冒险,虽然写作的时候是坐着不动的,但精神世界一直在活跃,这是创作的快乐。
到了拍摄阶段,我一般不会拍3条以上,很消耗演员。在拍之前我们会进行深入沟通和排练,尽量保证能1条过就只拍1条,不要超过3条,《老兽》就是这样的,我会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尽量保证拍摄的时候高效一点。
当然也有意外,比如沙漠的戏,湖水的涨幅我们是不知道,去了之后傻眼了,水涨到帐篷旁边了,只能等,每天看水位表,等到合适的时候再拍,但是天气已经很冷了,机器和人都不太扛得住,这些是控制不了的。
最后这部电影呈现出来的,吵架戏我是满意的,还有烧帐篷前后的戏,恐龙园里那几场戏,我都挺喜欢的。遗憾的是,如果当时用双机位来拍摄,我可能会有更多的素材,镜头的丰富性可能更强一些。
“黑血”放出来之后在《乌海》里,钱仍然是人物困局的重要原因。我特别在意价值观层面对于这个主题的探讨。这些年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好像变得有点扁平化了,好像钱变成了很重要的评价标准,不管在大都市还是偏远的地方,评价一个人、一个家庭的主体是偏向钱,情感都是其次的。
“你干什么工作?一个月赚多少钱?”这些大家都会经常地被问到。电影里也是,杨华的岳父出场就说工程款的事,杨华的父亲见他回家也最关心“恐龙公园的项目”,对人本身少了很多关心。钱成了最在乎的东西,如果社会把钱看得这么重要,还挺可怕的。
这个电影的残酷也在于此。我做的时候就知道,《乌海》比《老兽》要残酷,《老兽》是有苍凉和无奈的东西,但《乌海》把极端情况都加在了一个人的身上,看起来特别残酷。未必所有人都对残酷的东西有共鸣,我反而是想以这样的方式让人获得更大的警醒和反思。
这也是我最想和观众沟通的部分:我希望大家看过电影后,对情感、生活和自己的价值观,有所启发。
前段时间我听说英国有一个权威机构提出,情感问题发生变化一般由三个原因导致。第一是权力的介入,在电影里是杨华老丈人的干扰;第二个是经济问题,就是杨华身上巨大的债务危机;第三是两性问题,类似于电影里杨华和苗唯之间的感情关系等等。
同时也有刚刚提到的,社会价值观单一,整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下给人的压力,人精神的匮乏之类的问题,所以大家看完《乌海》后或许可以思考,我们应该怎么对待身边的人?是不是要那样冷漠?人和人之间的误解有没有更好的处理办法?我们应该更看重的东西是什么?我还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点思考。
《乌海》上映后,我当然希望票房有所成就,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做电影要先过自己这一关。比如《老兽》时,最高兴最难忘的时刻不是在电影节拿奖,而是杀青前一天,我和涂们老师坐在他的屋里,两个人都开心地笑了,就觉得这个电影成了;初剪看完后,我自己默默流了一会泪,我觉得这个电影是有力量的,这才是核心。
《老兽》
这次在看《乌海》第一版剪辑之前,我还是每天都痛苦的,但是看完初剪一下子就轻松了,觉得努力没有白费,值得了,这一刻是最重要的,我给了自己一个交代。
回过头来看,我估计这辈子拍的最残酷的电影就是《乌海》了。这部电影之后,我创作的第一个阶段就算过去了,接下来要进入第二个阶段了。
在第一个阶段里,《老兽》和《乌海》身上,可能放了很多自我的生命体验和本能的表达,这个表达在我们(内蒙)方言里“放黑血”,也可以是叫“放瘀血”。我小时候我们经常听到,一个人如果手腕这里正好有内伤没有破,里面有淤血的话会有一根红线,一直走到心脏,就完蛋了,很可怕。
只要划开口子,把血放出来,人才会好。我觉得前两部电影对我的意义就是放出了黑血,不放的话我可能就在第一个阶段过不去了。现在我把我过去生命里最残酷的东西表达了出来,接下来才能迈入更客观和成熟的状态去看待电影。
在我的想象里,第二个阶段的我,希望作为一个导演,能有强烈的个人风格、稳定的类型、一定的市场,有自己的美学和表达,观众也能喜欢。
下一部片子类型会更重一点。我不认为重类型就做不出好电影。现阶段的中国电影很像好莱坞的90年代,工业体系慢慢完善,类型电影有了一定的市场,创新和拓展在发生,新的电影语言和风格在树立——我们这代人正处在这个阶段。
现在整个市场和行业对于年轻的创作者,还是认可的,也在持续地支撑大家创作,只要项目足够好,市场都可以接受,这是很好的机会。困难的地方在于创作力,真正有创作力的人很少。
我觉得《乌海》跟《老兽》相比,导演的风格更加成熟了,但是我下一部电影肯定跟这个不一样,我想建立我自己的风格,而不是说“很像某某导演”。
虽然《老兽》之后,找投资确实比以前容易了一些,但也有难的地方。我想拍自己的项目,不想只做外面递来的项目。所以自己一边写作,一边面对现实的困难与创作的困难交织,很痛苦,但想着马上要启动新项目了,有一种憋劲的感觉——
在巨大的残酷里面,有着巨大的信心,人生和拍电影都是如此吧。
关键词: 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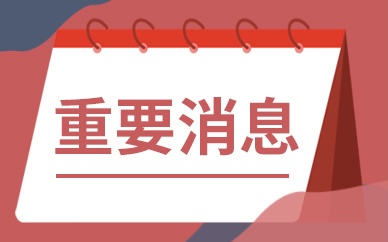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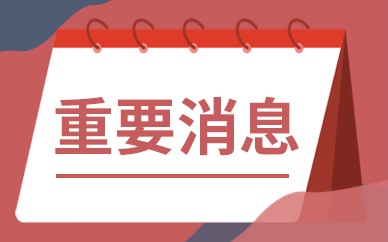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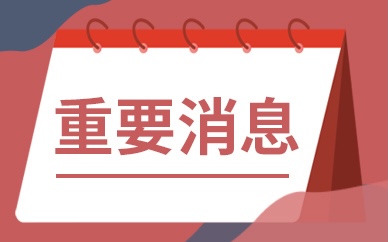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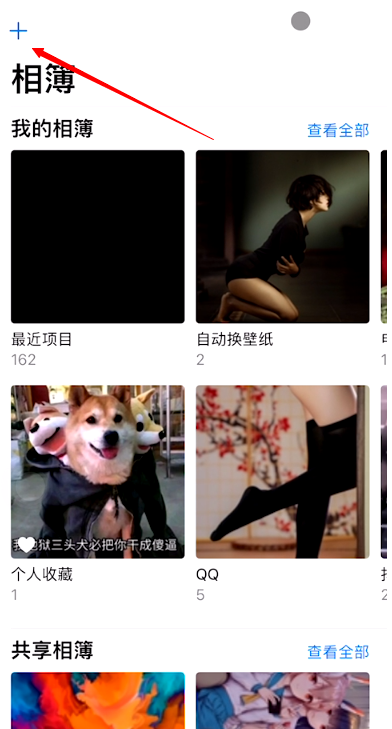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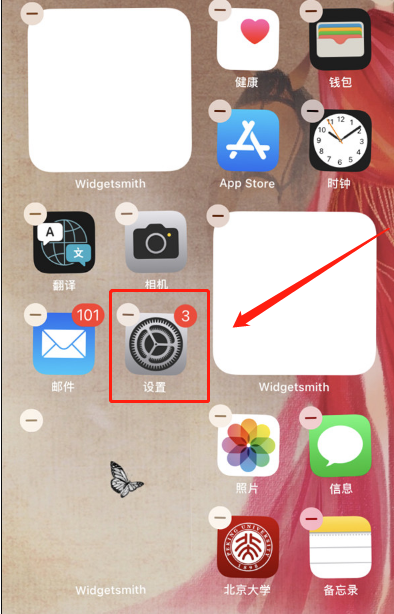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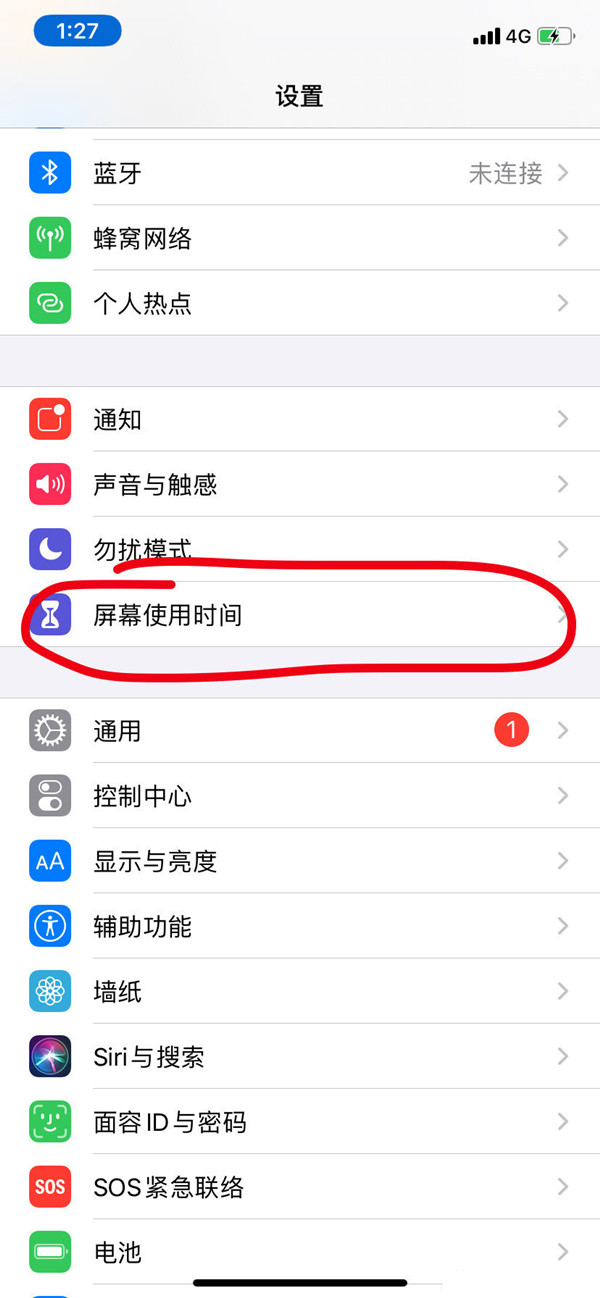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