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清水秀的幽静之地,一个木屋,一个院子,养花、种菜、有猫狗相伴,远离尘嚣,岁月静好,这是否也是你憧憬的生活?
在豆瓣“我们都渴望隐居”小组中,就聚集了这样一群人,“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他们试图逃离高度内卷的城市文明和996的职场高压,像梭罗一样,寻找离群索居、返璞归真的“瓦尔登湖”。
隐居,更像是通过逃离世俗的方式,去寻找和重塑自我。正如梭罗所说,“大多数人,在我看来,并不关爱自然。只要可以生存,他们会为了一杯朗姆酒出卖他们所享有的那一份自然之美。感谢上帝,人们还无法飞翔,因而也就无法像糟蹋大地一样糟蹋天空,在天空那一端我们暂时是安全的。”
不过,向往者众,行动者少,摆在眼前的现实障碍不少。
第一道关是钱:攒多少钱才能隐居,隐居后的收入来源是什么?种菜砍柴的辛苦,远离人世的孤独,不是谁都能忍受,找到合适的隐居地也不容易;
接下来是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不工作会不会焦虑,长期跟社会脱节有没有风险,离群索居是不是安全,社保断交怎么办?
还有一些软性的阻碍,隐居意味着一定程度上放弃世俗生活,父母的反对和催婚,亲友旧识的非议等等…..
总之,隐居是不少人感性的憧憬,但在道道难关面前,隐居只能是慎之又慎的理性决策,也只有极少一部分人才能践行。我们找到了几位行动起来的年轻人,他们展示了隐居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不体检没社保,种菜打柴自给自足,却逃不过父母催婚守静,90后,隐居湖南乡村4年,三人同行
守静隐居时26岁,但这个念头早在高中就模糊的出现了。
应试教育的压力让守静高中就开始失眠,毕业后又接着熬夜加班,连轴转了4年后,身体开始发出信号:眼睛干涩、腰酸背痛,更可怕的是长期无法改善的失眠。
守静看到了生活的尽头:身体一步步垮掉,要么得大病,要么就是一身小病。
守静的境况只是缩影。一份《部分城市居民健康状况调查报告》称:55%受访者睡眠状况较差,25%的受访者感觉生活和工作压力很大。
首当其中的就是健康风险,2019年1月发布的《中国中青年心脑血管健康白皮书》显示,20~29岁的心血管病高风险人群占比已经达到15.3%。
年轻人拿命换钱值不值?守静开始反思。
幸运的是,守静的身边还有两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她们都有一个瓦尔登梦,对城市喧嚣感到疲倦,向往宁静清澈之境。
“也不记得是谁先提出隐居的想法了,反正一拍即合,经常趁着节假日外出寻找隐居地”。三个姑娘先是在重庆附近的农村考察过多次,又深入秦岭、终南山、广东山区,花了两年多都没找到理想居所。
直到某次去秦岭徒步旅行,偶然遇到一所废弃的房屋,户主搬迁到了镇上,她才跨出了隐居的第一步。但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因房子被拆迁,不得不再次搬家,经过长距离的多次考察,守静最终搬到了湖南。
守静看中的位于秦岭附近的废弃房子
中国的地形与气候条件丰富多样,四季如春型如云南、两广、海南一带,四季分明型就更多了,选择多样,但找到合心的仍需运气。
守静的要求很简单,环境幽静、空气清新、有菜地、有柴有山就满足了, “风景不重要,去过的地方很多,风景都看够了,供暖也不必要,冬天我喜欢通过挖地、劈柴、运动等方式取暖,既能锻炼身体,又不至于陷入慵懒怠惰,但求四季分明,能体验不同的风物感受,而且有冷热循环对身体也是好的”。
三人都是行动派,自从决定隐居后,她们就没再纠结过,遇敌杀敌,遇佛杀佛,不达目的不罢休。
但父母坚决反对:首先是安全,山里会不会有野兽、毒蛇?女孩子住会不会遇到坏人?然后是事业和家庭,年纪轻轻跑山里去,一不上班二不结婚生子,这怎么行?
“前一点质疑还好应付,我们住的地方算不上深山老林,浅山地带最威猛也就是野猪了,但野猪主要吃素,不会刻意攻击人。至于坏人,现在农村街道已经有监控摄像了,犯罪成本太高,何况村里多是老人孩子,我们三个健康灵活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守静对父母循循善诱。
但后一个质疑就不易回应了。4年的隐居生活,守静大部分靠积蓄维持,偶尔网上做翻译赚点外快。她也一度担忧过,长时间没收入会不会焦虑?几年后会不会和社会脱节?
这是每个隐居人要面对的生存问题。被城市文明喂养的现代人回归自然,拿什么技能去换生存资料?
守静的处理之道颇为佛系,“当下和未来之间隔了很多时间和空间,只有走近了才能看得到,想不清楚那索性就亲自去试试吧。”
“尽人事,听天命”是守静的策略,但对父母而言,这无法成为安慰。他们无法理解女儿为何放弃稳定的工作,拿起锄头种地,挥舞斧头劈柴,成为满手起茧的“农人”。
但守静对此甘之如饴,她从劈柴挑水、翻土犁地、除草种菜的劳作中,找回了久违的踏实感,手上碌碌但心思空空。
三人搭伙儿,过得有声有色,种菜是最关键的“公共事务”,这决定了能不能吃上饭。厌倦了城市各种化学物质,她们追求原生态,拒绝农药化肥,自学防治虫害,一年光南瓜就收获了几百斤,吃不掉的背到山下去卖,卖不出也不着急,索性就烂在地里做堆肥。
守静三人的种菜笔记
山里的生活开支不大,房租一年1000元三人平摊,蔬菜自种,需要买的只有粮油米面、日用品,连护肤品也不用,冬天只抹一点甘油,“美好的心情、健康的饮食、规律的作息、干净的环境才是最好的护肤品”。
起居标准也降到最低,捡来木头搭几个搁板就是衣柜,竹子捆几下就成了鞋架,家电只有烤箱和锅。连冬天下山洗澡的花费都免了,室内用塑料膜搭个临时浴室就搞定了,可谓家徒四壁。
“来到山村就别想着购买力了,我本就不是奔着世外桃源的浪漫去的,主要是为了追求健康的环境和省察内心的契机,心态放平了就觉得有吃有穿,有理想的朋友,有遮风避雨的住所,就真的很幸福了。”
自制“衣柜”和手工马扎
她们也不缴纳社保,不体检,守静有自己的理论——小病不用治,大病没钱治也不易治好。“相比医院,我更相信进化了几亿年的身体免疫系统,自己保障健康和安全才是掌握命运的开始。”
这样的极简生活,花不了多少钱,“一年不超过一万,如果要隐居个三五年,只要攒够几万块就行了。”
前两年守静专心恢复身体,每天练瑜伽、八段锦、冥想、睡觉,其余时间用来生活:做家务、种菜,爬山探索,就这样长达10多年的失眠,竟被彻底治愈了。
身体的本钱有保证了,才有心思考虑未来。
这两年守静开了个名为“守静隐居”的公众号,分享隐居生活和感受,她并不想吸引观众,只期待与志同道合的朋友碰撞交流,同时又能探索挣钱的可能性。
更远的事她就没打算了,正如当初隐居时就没有刻意筹划一样,“什么时候不想了就回到城市,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青山对我来说就是身体、思维架构、心态,先把这些通达了、理顺了、放平了,其他自然而然会来。”
她很清楚这样的神仙日子不可能长久,“钱花完了还没找到生存道路自然是要去工作的,目前打算再隐居个一两年,可能会去四季如春的云南或海南考察,也会逐步跟外界交流,看情况吧,不想太远的事,大多数人正是因为每天为未来谋划才错失当下,所以我的理念是过好今天,持续改善身体和丰富认知,未来就不会让人失望。”
前猎头30岁隐居乡村,再不行动就没机会了安雅,隐居成都乡下2年,两人为伴
安雅快30岁时决定隐居,对她来说,30岁仿佛是一个分水岭,如果还不做出点什么改变,以后恐怕就更没勇气了。
隐居的想法起始于大学毕业,但那时资金、阅历都比较欠缺,内心也不确定这就是自己想要的。
热爱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安雅一直酷爱大自然,爬山、露营、徒步。毕业后她穿梭于多个城市,最后定居在成都。在她看来,成都有草原、荒漠、雪山,包容性高,风土人情很有吸引力。
隐居的契机正是来自某次偶然的户外行,她和朋友在成都周边游时看到一个院子,很是喜欢,两人坐在村头的稻田边聊了很多,当场便决定租下来。
乡下没有外卖,必须学会“自给自足”
和守静不同,安雅原来的工作并没有很大压力,她做猎头,在公司的业绩非常好,离职时领导一直挽留。但升职加薪,并不是安雅想要的,“做猎头就算我做到VP级别,也不怎么高兴。”
所以奔赴山村,并非逃避和厌倦,纯粹是心之所向,“村里没有高楼大厦,地广人稀、视野豁达、人际交往简单,加上我性格喜静,爱独处,爱养猫猫狗狗,大自然和小动物两全其美,这让我感到平和舒适。”
即便自我认知如此清晰,做决定也是不容易的,安雅也不免顾虑,“我并非技术性人才,不知道靠什么维持生计,在这种情况下,也顾虑父母的想法,一没收入,二年龄大了还没结婚,说服他们很难。”
剪不断理还乱。30岁的迫近给了安雅临门一脚的勇气,她等不及了,没有答案也要上路,“不如破釜沉舟试一次,给自己五六年的时间,如果还不能解决收入问题,再回城市上班”,这是她心理上的退路。
但她清楚这条退路有多难,五年后自己恰好35岁,30+未婚未育女性的职场困境,她见多了。
大部分公司出于对婚假、产假等成本的考虑,面试30+未婚女性时,总会问到“什么时候结婚?”,“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等个人问题。所以有人调侃,各行各业都在内卷,但30 +未婚女性连内卷机会都没有。
不过,安雅想得透彻,“那是或早或晚都要面对的,我只是把压力提前到30岁,在更年轻的状态下去探索。”
她相信自己不会走到潦倒无望的一天,辞职前她只做了健康方面的托底准备——一次全身体检,配了一个百万医疗保险,就义无反顾了。
没想到刚住进去,就碰上暴雨,房屋年久失修很快就漏得滴滴答答,原定的铺地板、安装床铺等工程,只能搁置。安雅和猫狗挤在一起,住了十多天地铺。
屋顶修好后,换到新环境的不适感又开始躁动,大多时候无人疏解,只得等时间慢慢疗愈。
修整乡下的旧房子
善于独处是隐居者的必备技能,隐居地多为山里或村里,周围人烟稀少,也没娱乐设施。大把的时间一个人怎么捱过呢?看综艺刷抖音未免消沉,也违背了隐居初衷,只修身养性也会疲劳乏味。
安雅有自己的心得:要有多种爱好来切换,不然很容易在安逸中颓废,闲下来也容易焦虑,这就丧失了隐居的意义。她把小日子安排得满满当当:看书、种菜、跑步、爬雪山、改造家具、做猫爬架、腌鱼、酿酒、养鸡仔、捡流浪小动物、赶集...
种菜是不少隐居者的普遍选择
时令的仪式感被她安排得像一幅画卷:立夏的鸡蛋、小龙虾,中秋的月饼、大闸蟹,冬至的水饺,跨年夜的篝火“派对”、春节的对联、年夜饭,安雅让生活彻底融进四季中。
和守静的修养身心不同,安雅的隐居更像是践行三餐四季的生活本质。但再诗情画意的生活,也免不了现实的拷问——钱从哪儿来?
安雅每月必要的开支包括:房租750,医保400多,生活费500左右,猫粮100多,偶尔的人际来往500左右,还要余留一部分用于小病就医等风险,杂七杂八加起来每月要有3000左右的进账,才能满足最低预算。
安雅尝试过写作投稿,但自己并非专业出身,而且稿费太低;
帮朋友运营公众号,觉得仍是在给别人打工,挤压了原本属于自我的时间空间;
想过做线上店铺,但找不到合适货源,自己又没有经营头脑;
爱做手工,钩织包包、鞋子等作品出售,带来一点点收入,但很不稳定;
学习烘焙,尚未变现,大多是请朋友免费品尝。
安雅的手工作品难以稳定变现
没解决的不止生计问题,还有父母的担忧。父母与她促膝长谈换来的临时开朗,回头在亲戚们的频繁“关心”中,又再度被焦虑取代。
安雅觉得,两代人的观念永远达不成和解。这也是她选择不回老家隐居的原因。她坚信生活的意义要由自己来定,正如她在朋友圈的叩问——“你是生活意义的创造者?还是一个二手货?”
她从不担心年龄渐长会是情感的障碍,而且有了丁克的模糊念头,虽向往知心伴侣,但一切顺其自然。“按这个趋势,父母的担忧大概率要成为既定事实了,但其实我并没有刻意要成为少数人,不走到那一刻,我也不知道会衍生出什么想法。”
面对现实难题,她和守静共同的策略是:不想太远,关注当下,信任自己有处理好未来各种境遇的能力。这也许是她们面对不确定也能付诸行动的关键内核。
隐居不敢躺平:开民宿投资十万,年进账两千周铭,90后,隐居北京郊区2年,一人独居
周铭隐居前做了5年的自由摄影师,他带着2只猫住在北京市中心仅有9平米的老旧胡同平房中,月租只有500,后来平房要拆迁,周铭才下了决心。
自由摄影师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职业,但就像律师有钱的占比不到一成一样,周铭不是有钱的少数派,收入很不稳当。但他不肯为赚钱牺牲自由,“我一直很穷,但又不爱上班,所以就这么维持着现状。”
搬到乡下住的念头三四年前就有了。他虽在城市长大,但从小就知道乡下好玩,植物、空气、水、阳光、安静的环境、健康的食物,这些城里没有的氛围感,深深吸引着他。
但人都有惰性,被现状驱动着往前跑,而且下乡也有风险,所以这个念头一直搁置了多年。直到平房拆迁,城里找不到便宜的房子,再不行动就无处可归了。箭在弦上,周铭决定出发。
他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凡事都有风险,反正人生已经穷到底了,再“混”几年试试,要是失败,那就回去上班。
和守静、安雅不同的是,一开始他就想好了要利用乡下条件赚钱:做乡野私房菜和艾灸养生,“乡下独特的环境走养生策略,应该很有机会,而且我平时就积累了艾灸和做药膳的技能,对转化能力有信心。”
一直“喊穷”的周铭,却在北京郊区租了个更贵的房子作为“乡村事业基地”,150平的毛坯房,一年三万租金。第一年断断续续的装修,花了10万左右,除了积蓄还借了不少钱。
北京郊区的一些民房也不便宜
谁料开张后只接待过几个客户,就碰上疫情封村了,花了10万多元的成本,最终只有一两千的进账,周铭只好边维持边另寻他路。
本着“靠山吃山”的策略,他盯上了村子附近的皂角树,尝试开发植物皂角洗涤剂售卖,方法是现学的:把皂角泡软——煮好打碎——将浓汤晒干——捏制完成,长期自由职业的他习惯了自己找路子。
隐居不是躺平,比起打工,隐居需要更多拥抱变化的适应性。
周铭自嘲是“正宗首都乡村贫困孤寡老人”,赚钱能力一直是他的短板,但并不影响他的生活热情。
在大众看来粗陋窘迫的乡下生活,却处处令他欣喜,为了节省开支而做的种种探索,也带来别样趣味。
种菜是节省的必选项,周铭学着种胡萝卜、南瓜、番茄、豆角、秋葵等作物,吃不完的晒成南瓜干、萝卜干、豆角干。遇上旱涝收成不好,或者被野猪偷吃时,周铭就去山上挖野菜,荨麻、槐花、野葱、苦菜,连白菜帮子也不舍得扔,风干后用山楂酱泡几天就成了“周式酸白菜”。
经常出现在周铭菜单上的是:胡萝卜干拌面、生白菜叶拌面、槐花汤面、烤花生萝卜饭、果丹皮拌饭、自制土豆面包......不能说是苦行僧,但也是很多人无法下口的。
周铭自制简易“烤箱”
当事人却不以为意,“来到乡下才知道以前在城里有多苦,现在有猫揉、有瓜吃、有包啃、有花看,就是很好的生活了。”
周铭一个人住,但从没有孤独感,他得意的说,“我社交能力好的很,能跟任何人聊天,社交困扰是不存在的。”
他也善于自己找乐子:
用木棍做了把“明式交椅”,连猫都不稀罕赏光,只好沦为朋友圈展览的艺术品;
周铭的自制椅子并不实用
用旧砖、黏土、草杆制作火箭炉烧炕,再放上个不锈钢大盆就成了兼职烤箱;
为了省水,研究出用平行沟和星形沟在旱地种红薯苗;
为了偷懒,发明了全程不沾粉不沾水只用筷子的懒人面包;
喜欢木工,就把平底锅、健腹轮都换上木把手;
面对父母催婚,周铭也学会了“避实就虚”,“结婚我不拒绝啊,但也没人要跟我结婚啊,找来找去很花时间的,而且生怕不合适还得离婚惹父母生气。生小孩嘛,有钱可以生,所以还是穷,这样说就没问题了。”
现在,周铭的私房菜已经恢复营业,皂角洗涤剂的探索也在继续,赚钱之道尚未走通,不过,即便赚不到钱,他也愿继续“游戏乡间”。
周铭正在试做纯天然皂角洗涤剂
会永远隐居下去吗?周铭也不知道,毕竟,坚定的自然主义者梭罗,也仅在瓦尔登湖旁边逗留了两年,就重新踏入了熙熙攘攘的世俗生活。
(文中采访人物皆为化名)
关键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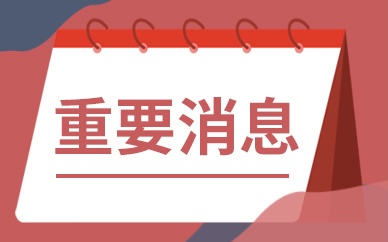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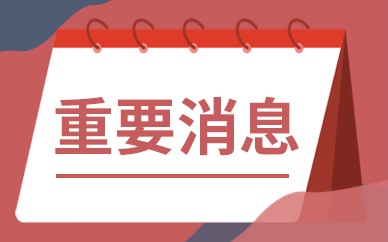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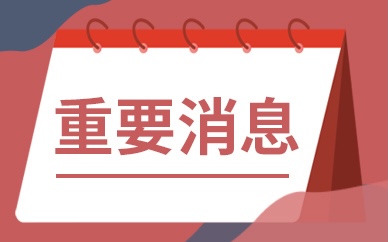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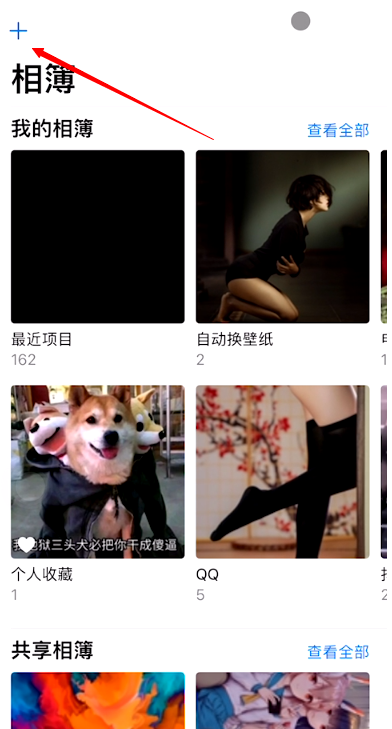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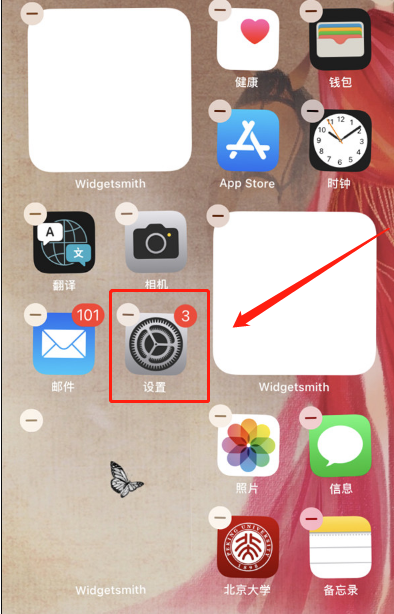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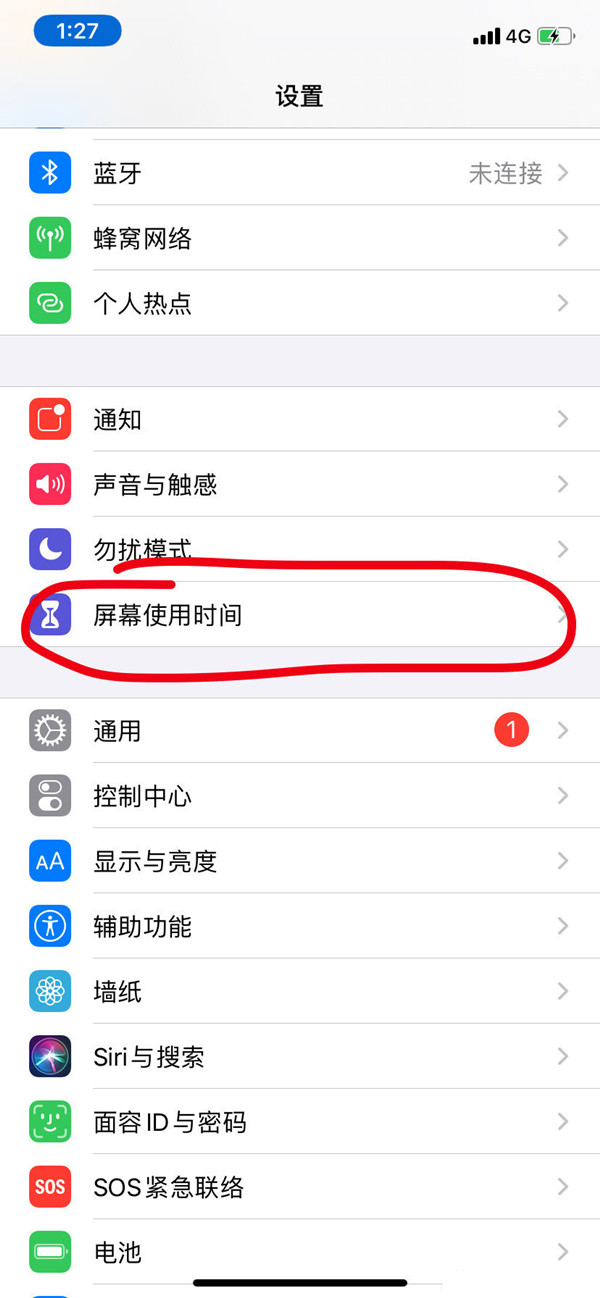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