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论坛】
作者:杨芹(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朱熹最重要的思维方式之一在追本溯源、格物穷理,这种思维方式投射到诗学领域,主要体现为对诗歌的本质、终极价值、终极影响因素、终极审美理想的探索与认定。就影响因素而言,朱熹认为创作主体的综合素养对诗歌成就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朱熹认为创作主体的德业情操尤其是对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伦大法的态度从根本上决定了诗歌的品位与传世价值。淳熙十二年(1185年)二月他在《向芗林文集后序》中传达了两层意思,一是明确宣示了自己的价值观,认为“天命民彛、君臣父子大伦大法”乃古今大节大义之所在,“大者既立,而后节概之高、语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若大节有亏,小节小义、诗词文章便无足挂齿,此乃古人“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之说在朱熹思想中的投影。在其看来,纪逡、唐林纵有忠直苦节之名,王维、储光羲之诗纵有修然清远之貌,一旦失身于王莽、安禄山政权,那么他们穷尽终身辛劳所获得的一点能够流传后世的名节与诗歌也不过是供后人嗤笑的谈资罢了,与之相比,张良、陶渊明、向子[~符号~]这些始终秉持君臣父子之大伦大法者才是真正的大节大义之士,他们的节概文章才真正具备不朽的传世价值。二是认为创作主体本身的德业情操决定了其诗歌品位,比如陶渊明平生虽无多少功名事业可言,但他自以晋世宰辅子孙而不肯屈从刘宋政权的高情大义投射于诗歌之中,其诗便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向子[~符号~]比陶则又多了一份施展抱负的机会,他一生不仅始终固守君臣大义,而且以重臣之位为国家社稷立下汗马功劳,即便病重垂死之际仍坚持劝谏君王勿忘国耻与复国大计,中年虽自放于江湖之上,终不失其清夷闲旷之姿、魁奇跌宕之气,而这种大气魄注入诗歌之中,“虽世之刻意于诗者不能有以过也”。在朱熹看来,向子[~符号~]能够为诗歌注入“清夷闲旷之姿、魁奇跌宕之气”的根本原因并不在其绝俗离世之举或发兴吐词之工,而在其烈烈德业。正是德业在前,绝俗离世之举、发兴吐词之工才真正有所依托而不至流于虚妄卑弱,这也是朱熹诗学思想的时代价值与历史价值之所在。
其次,朱熹认为创作主体内在的情性资禀与胸襟气度决定了诗歌的风韵气骨与言辞风貌。如弟子问:“‘《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诗人情性如此,抑诗之词意如此?”朱熹答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词气声音。”(《朱子语类》卷25)庆元四五年间又云“唐明皇资禀英迈,只看他做诗出来,是什么气魄!今《唐百家诗》首载明皇一篇《早渡蒲津关》,多少飘逸气概,便有帝王底气焰!越州有石刻唐朝臣送贺知章诗,亦只有明皇一首好,有曰:‘岂不惜贤达,其如高尚何’”,“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语类》卷140)所谓“本相”,在此指个体的真实情性与真实意志。在他看来,陶渊明本非平淡之人,故而不可能写出真平淡之诗,平淡只是其诗歌的表象,陶氏内心的本象决定了其诗歌根底上的真豪放;同理,唐明皇诗歌之所以呈现出飘逸的大气魄,亦是源于其内在资禀的英伟豪迈,同样是送贺知章诗,朝臣便写不出明皇诗中的帝王气韵。基于这种观念,朱熹不仅提出“诗见得人”说,还将诗歌的语言风貌、内容意旨作为推断作者身份之依据,认为“《大雅》非圣贤不能为,其间平易明白,正大光明”“《风》多出于在下之人,《雅》乃士夫所作。《雅》虽有刺,而其辞庄重,与《风》异”“《关雎》之诗,非民俗所可言,度是宫闱中所作”(《语类》卷80、81)。
再次,朱熹认为创作主体的学养决定了诗歌创作能力。其晚年曰:“今人学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费了许多气力。大意主乎学问以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诗亦然。”(《语类》卷139)这番话后世多理解为“只要明理文章自然就好”,但实际上“明理”“自然发为好文章”的前提皆在于“主乎学问”,朱熹强调的是学养功夫。他认为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与其枉费气力去学写文章,不如将重点放在读书问学上,学养深厚则事理洞明,写起诗文自然得心应手。这种思想朱熹还有许多类似表达,如“贯穿百氏及经史,乃所以辨验是非,明此义理,岂特欲使文辞不陋而已?义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则其存诸中者必也光明四达,何施不可?发而为言,以宣其心志,当自发越不凡,可爱可传矣。今执笔以习研钻华采之文,务悦人者,外而已,可耻也矣!”(《语类》卷139)
最后,朱熹认为诗人创作时是否拥有“虚静而明”的心境决定了诗歌的精妙与平庸:“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缘不识之故。只如个诗,举世之人尽命去奔做,只是无一个人做得成诗。他是不识,好底将做不好底,不好底将做好底。这个只是心里闹,不虚静之故。不虚不静故不明,不明故不识。若虚静而明,便识好物事。虽百工技艺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虚理明,所以做得来精。心里闹,如何有此意?”(《语类》卷140)在他看来,事情做不好是因为“不识”,“不识”的原因在于“不明”,而“不明”则因“心里闹”“不虚静之故”。即便是百工技艺,也唯有“心虚理明”,方“做得来精”。作诗亦是如此,唯有“虚静”方能“做得成诗”。
综上可知,朱熹分别从个体的德业情操、情性资禀、胸襟气度、学养积淀、创作心境等方面凸显了创作主体对诗歌之品位、价值及审美风貌的决定性影响。在其看来,创作主体的综合素养是决定个体诗歌成就的内在因素与首要条件,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绍熙二年(1191年)夏其《祭南山沈公文》一文中:
(沈公)气象严伟,凛若泰山之不可踰;而情性端静,劬然蠹鱼之生死于书。家徒长卿之四壁,而清恐人知。嗟乎叔晦!学问辨博,识度精微。官止龙舒之别乘,而才实执政之有余。人皆戚戚,君独愉愉。人皆汲汲,君独徐徐。而惟以道德为覆载,以仁义为居诸,以太和为扃牖,以至诚为郭郛。至于大篇短章,铿金戛玉,钩玄阐幽,海搜山抉者,又特其功用之绪余也。
在朱熹的人物评价体系中,较为鲜明的特点是以“气象”论人,首论道德、情性,次而学问、识度,次而才华、事业,最后才是诗词文章。在其看来,诗词文章是个体素养水到渠成的结果,品性、学识、才华、事业不仅决定了个体的气度风貌,“至于大篇短章,铿金戛玉,钩玄阐幽,海搜山抉者,又特其功用之绪余也”,换言之即创作主体的综合素养之于诗文乃是根与花、源与流的关系。因此,朱熹论诗文往往更为看重创作主体的修养,其次才是作品的审美风貌,认为前者乃后者的根本,有前者方有后者。
实际上,强调创作主体综合素养对诗歌的决定性意义并非朱熹的个人独见,苏轼“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送参寥师》)、陆游“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示子遹》)、严羽“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及其至”(《沧浪诗话》)所表达的意思与朱熹相似,不同处在于就创作主体的综合素养而言朱熹更为强调“德”的首要地位,认为“德”对诗歌的品位与传世价值具有一票否决权,而“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伦大法”作为“德”的第一要义,不仅对内可体现为性情上的温厚宽和,对外亦可发散为诗歌的词气义理之美。这种诗学观念不仅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对于当下诗坛与时代风气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因为诗歌永远应该是培育人们具有健全人格、高尚境界与审美情操的艺术样式,抛开对人的培育而仅仅关注文字的表达技巧与艺术效果,即便不说是舍本逐末,对于诗歌的理解至少也是残缺的。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26日 13版)
关键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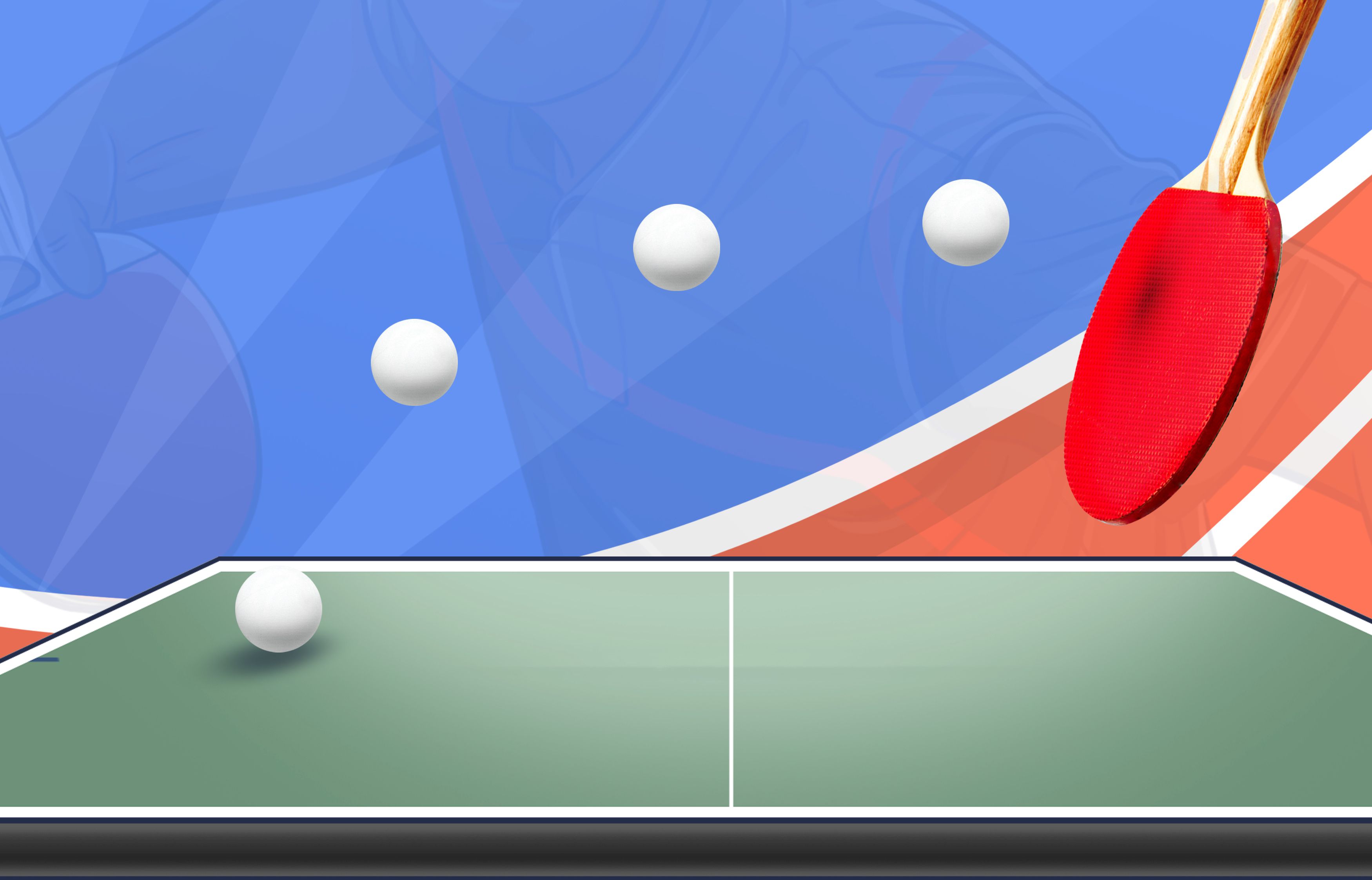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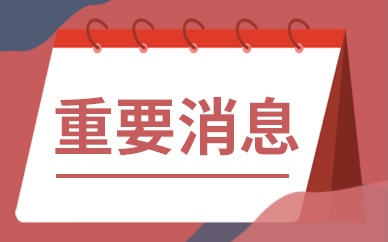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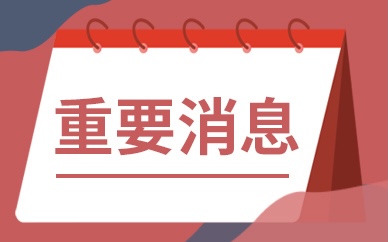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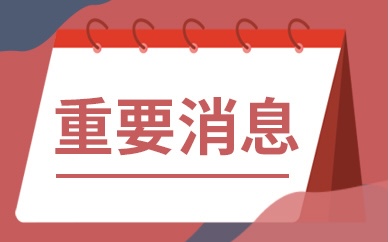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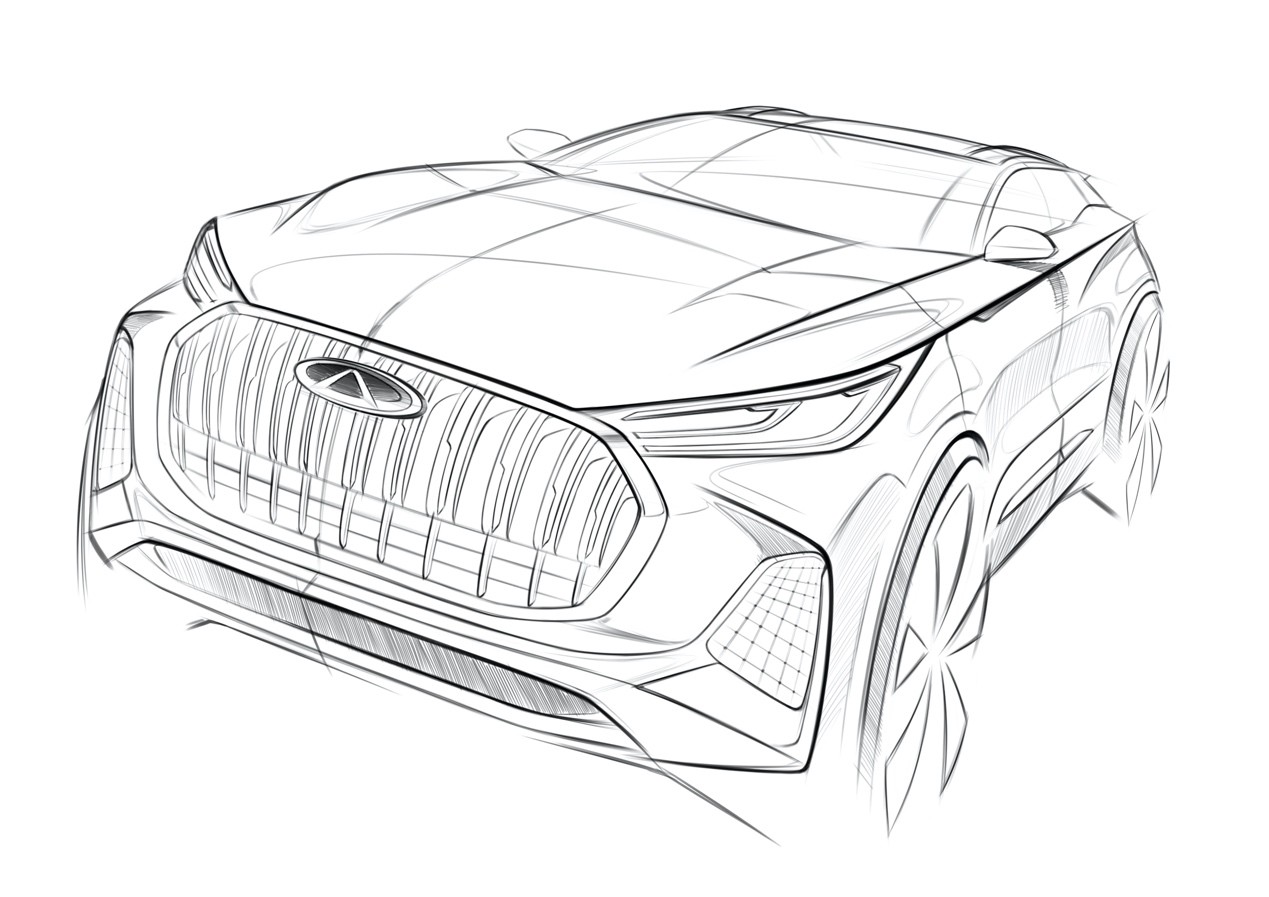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