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某乎曾经有个热门问题,“年轻人越来越不喜欢发语音了,如何看待这一现象”,问题描述中提出,很多人“认为经常发语音的人不是自私、没文化就是因为上了年纪”。
过去几年,在社交软件中发语音信息渐渐被认为是不懂社交礼仪、方便自己麻烦别人的表现。尤其是当语音信息时长长、条数多、信息量却少时,很容易让一些收听者崩溃,遑论在一些特殊场合听语音时不小心开启外放模式的尴尬。
然而,对某些群体比如年长者来说,语音确实是更便捷的方式。尤其对于常年说方言的群体而言,普遍使用的拼音输入法让发文字消息的难度变大,简直要分分钟重回小学语文课堂。
此外还有语音支持者认为,语音能够让人有亲切感。特别是对于不在一块的亲朋好友而言,能够通过手机听到对方的声音可谓是信息技术带给人类的一大幸福。更何况,没有语音功能,那和曾经的短信时代又有什么区别?
当下,随着语音输入、语音转文字、语音暂停和续播等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上语音消息和文字消息之间的差异也更加明显。本期全媒派将聚焦文字与声音两种基本媒介,对其功能及与使用者的双向关系提出更多的思考与探索。
语音与文字:最基本的交流方式诗歌《从前慢》中写道:“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 是一句”,而后又写道:“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短短的一首诗中涉及了交谈和书信,或者说语言与文字这两种最基本的交流方式。
根据英尼斯的“传播偏向论”,传播和媒介具有口头传播的偏向和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和空间的偏向。而麦克卢汉将其概括为,口头和耳朵的传播会受到时间束缚,而眼睛、文字、书面的传播会受到空间的束缚。
口口相传就是最典型的口语传播,但是很显然,这样交谈信息无法长期储存;而书信可以长期留存,却无法做到实时交流。我们有许多讲述书信交谈的浪漫故事,从书籍《查令十字街84号》到电影《玛丽与马克思》,主人公无一不是通过漂洋过海的书信展开漫长的交流。
但是在新媒介技术日益发达的现在,已经很难想象每发出一次消息就要等待几天甚至几个月、几年才能收到回复。技术让我们的沟通变得更加容易,也让我们越来越容易对“慢”不耐,我们期待着消息发出后能立即收到回复,甚至会有不少人认为对方回消息的速度反应了对你的重视程度。
数字时代的交际需求促使移动新媒体不断致力于构建完整的传播体系。学者姚劲松指出,“完整的传播体系=言语行为+非言语行为+传播情境”[1],移动新媒体中声音功能的开发和应用,显然是加强了传播体系中言语行为和传播情境的作用,激活并强化了社交媒体的口语传播属性。而这种属性又为口语传播行为提供了一个能够通过存储“留住时间”的中介物,使用者能够借此获得一种“中介形态的互动和体验”[2],交流也因此成为了一种中介化的口语传播行为,更为重要的是,曾经受到时间束缚的口语传播通过新媒介这一中介,突破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进而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永恒”。
学者董晨宇曾写道:“在面对新媒体时,需要把新生之事放进历史的脉络中,才能更为清晰地洞察到它的真正意义。”[3]对不断发展的社交媒体而言,从历史视角出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它们在当下的意义。论坛、微博中的留言板、评论与历史上人们留在城墙上的文字、对谈从本质上来看有着类似的性质,这似乎也在证明无论是古代人还是21世纪的我们,都有着相同的社交需求和社交本能,而不断发展的技术实际上既迎合和满足着我们的社交需要,也在适时改变着我们的社交方式和习惯,甚至进而影响文明的传播。
因此,探讨社交媒介中的语音传播和文字交流背后的逻辑关系,我们可以回到技术发展本身。
语音交流背后的技术发展和社交需求每一种新媒体出现时,人们总会习惯于先思考该如何理解它。
南希·K.拜厄姆(Nancy K. Baym)在《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中分析道,就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常见的观点有:技术决定论、社会构建论和社会形成论,其中技术决定论认为,社交线索的缺失和潜在的传播异步性,使得中介化传播的亲密性、人际交往品质下降,甚至会产生对抗性矛盾。进一步来说就是媒介提供互动情境的能力决定了媒介在沟通方面的可能性和对抗性,而有限的社交线索(或者说提供的互动情境)又会影响人、人际关系和社会阶层。[4]
如果我们用更生活化的例子来解释,可以通过比较面对面交流、通电话和网络文字交谈来理解:
在面对面交谈中,我们不仅能够听到对方说的话,还能看到对方的表情甚至肢体动作,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建立更深的感情,也因此会让交流更加私人化;
传统的电话交流中我们无法看到对方,但是可以通过声音判断对方的基本情绪,有助于建立较为私密的关系,但是情感层面上会弱于面对面;
网络文字交谈则是一种方便且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方式,但是也因为看不见、听不到,容易产生一种冷冰冰的感觉,同样的一句话、一个表情在不同的语境下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也因此是不太利于情感交流的沟通方式。
在技术决定论中,很多人会将媒介视作会沟通双方情感与亲密度的中介。这样的立场暗含着对社交媒介的不信任与指责。诚然,身体在场的交流往往意味着情感在场,而单纯依赖线上交流也可能会带来雪莉·特克尔所说的“群体性孤独”[5],但是人的能动性也使得人们能够将社交性注入中介化的传播里,进而表露情感、表达亲密和娱乐,并建立新的社会结构。
因此,拜厄姆指出:“中介化交流应该被视为一种新颖、兼容的混合交往方式,而不仅仅是具身(embodied)交流的缩减版本,因为它将面对面传播与书写交流的元素加以结合,同时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图像。”[6]他认为,与其关注中介如何影响传播,不如思考人们如何处理中介化的传播。
换言之,技术并不能决定人们使用它的方式,也许技术可以决定使用的起点,但永远无法决定使用的终点。人们对社交的需求背后有着情感交流的本能,这种本能会让我们在使用技术时不断有“情感补偿”行为,不少学者在研究各种人们对各种社交软件的使用行为时总会习惯于用“使用与满足”理论,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一点。
而语音社交较之文字社交,显然更符合受众的“情感交流”需求,正因如此,近几年也有越来越多基于语音的社交软件面市。即便在互动线索最贫乏的纯文本媒介中,人们也可以表达出情感与亲密性,也能享受交流的乐趣并建立种种社会关系,不过这依然不影响他们更喜欢互动性更强的媒介。
如今的数字媒介使用者多为年轻一代,他们成长于数字媒介迅速发展的时期,深谙互联网的生存之道,他们中的很多人拒绝不注重边界的过分亲密,却也期待能够孤独时刻得到些许情感抚慰。
许是因为如此,播客、听书等声音媒介在近几年得到了迅速发展,不需要看到脸,不会过度亲密,却又有声音传递情感,这的确符合不少年轻人的心理。而我们也需要看到的是,播客、听书等媒介“具备移动性、社交性、人工智能等多种智能媒介属性”,尤其是对听书的受众来说,“用户的有声书使用行为达成了人与人、人与事物、人与环境的交互。”[7]
显然,这意味着数字媒介中声音技术的发展又进一步迎合了场景传播的需求。
声音将回归主流介质?事实上,无论年轻人有多么厌烦在网络社交过程中听对方的语音,一个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在传统广播式微后,音频正在通过社交语音、网络播客、车载广播、家庭智能语音等各种方式回归主流传播介质。
从莱文森的“媒介进化论”理论看,媒介进化的规律在于复制真实世界中“前技术”的或是“人性化”的传播环境。[8]而有声语言与听觉传播显然是“前技术传播”语境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也意味着声音技术在网络新媒体与智能媒体中将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声音曾经被认为有不确定性、稍纵即逝性、线性传播性、信息容量有限等局限性,这也使得曾经的广播具有了非独占性与伴随性。在社会节奏越来越快的当下,这些特性越来越成为优点:人们要处理的信息越来越多样,因此对具有兼容属性的传播媒介的需求日趋强烈。而“声音信号利用的是‘边缘’注意力,只有当不同寻常的声音响起时,人们才需要注意到发生的状况。因此,声音的告知不造成过分负担——这成为听觉沟通的精髓”。[9]
喻国明等学者在用户对语音新闻感知效果的测量研究中指出,“‘声音’在未来传播中将回归主流介质”,而在网络媒介与智能媒介迅速发展的当下,“声音作为传媒业中人工智能技术的‘第一入口’,将使印刷术发明至今的‘视觉本位’的文明再度向听觉中心转变,将‘脱部落化’时代的人们重新拉回‘部落’。”[10]
近几年,随着AI技术的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家庭开始接入智能语音服务,小到智能音箱,大到“AI合成新闻主播”,声音逐渐成为日常的智能交互入口。
5G技术与人工智能将声音重新拉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而我们的社交媒介也在不断尝试在语音传播中设计更多的可能。这也说明,技术的不断进步提供全新的媒体可供性,进而影响交流的速度、交互性、可及性的改变,从而创造新的社交语境和文化。
毋庸置疑的是,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的媒介环境更加复杂,也让我们置身于一种复媒体环境中,而当这种环境又变为一种可进行传播的场景时,人们可能会面临新的社交挑战。
但从媒介本身而言,某些类型的媒介会更适用于某些特定类型的关系,不同的人也会根据自身需求以及沟通对方的特征来选择具体的媒介,换言之,无论技术多先进、媒介类型和使用方式有多种多样,能够决定使用方式和偏向的终究是我们自己。
从第一代传播技术发明到现在,人们依然会执着于思考交际、传播、媒介与自身的关系,进而构建更有意义的社交关系。也许有人会担忧社交中的媒介中介会影响我们的面对面交流能力,影响我们与他人的情感联结;也许也会有人认为新技术、新媒介能够让我们打破时间、空间限制,与我们在意的人时刻保持着联系。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无论技术本身如何,人都可以凭借适应能力和创造性对技术产生影响,用科技实现目标。也许有时候我们对媒介的一些解锁,是设计者都未曾想过的可能性。
回到文章最初的问题,发语音和发文字,背后从来都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两者更不是二元对立,一切均在于发消息的我们想要利用哪种中介化传播方式,建立与对方的关系。
参考资料:
[1]姚劲松.新媒体中人际传播的回归与超越——以即时通讯工具QQ为例[J].当代传播,2006(6):53-55.[2]杜志红.被中介的口语传播:声音之镜与时空偏向——基于对微信语音的考察[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91-94.[3]董晨宇,唐悦哲.社交媒体中的交往与想象,引自《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译者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7.[4][6][美]南希·K.拜厄姆.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M].董晨宇,唐悦哲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7.[5][美]雪莉·特克尔.群体性孤独[M]. 周逵,刘菁荆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3.[7]戴元光,夏寅.莱文森对麦克卢汉媒介进化论思想的继承与修正——兼论媒介进化论及理论来源[J].国际新闻界,2010(4).[8]姜泽玮.内容、形态、场景与满足:移动新媒体有声书的用户使用研究——以移动应用“微信读书”与“微信听书”为中心[J].出版科学,2021(5):31-40.[9]艾媒网.2017-2018中国在线音频市场研究报告.https://www.iimedia.cn/c400/61111.html[10]喻国明,王文轩,冯菲.“声音”作为未来传播主流介质的洞察范式:以用户对语音新闻感知效果与测量为例[J].社会科学战线,2019(7):136-145+282.关键词: 社交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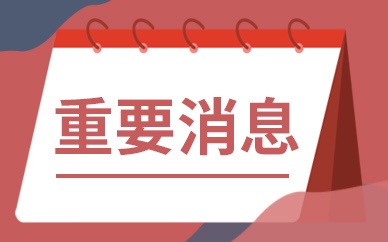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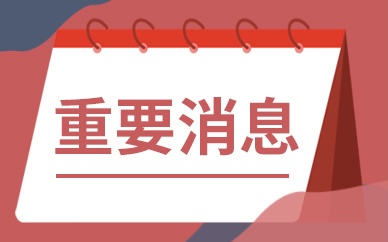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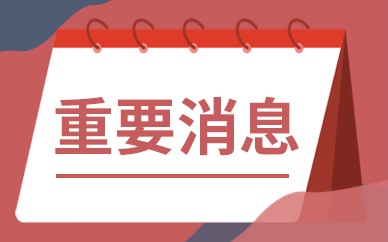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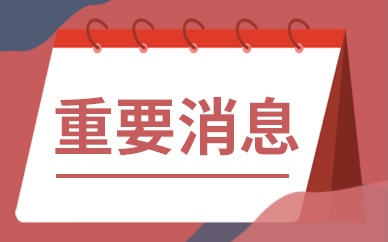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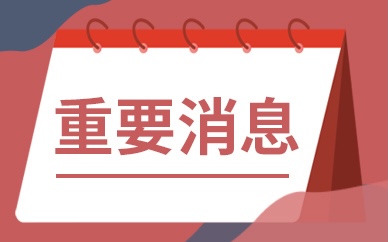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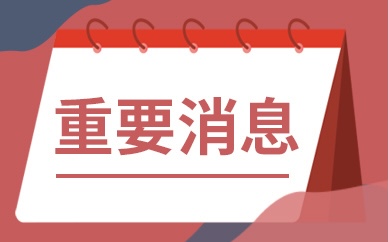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